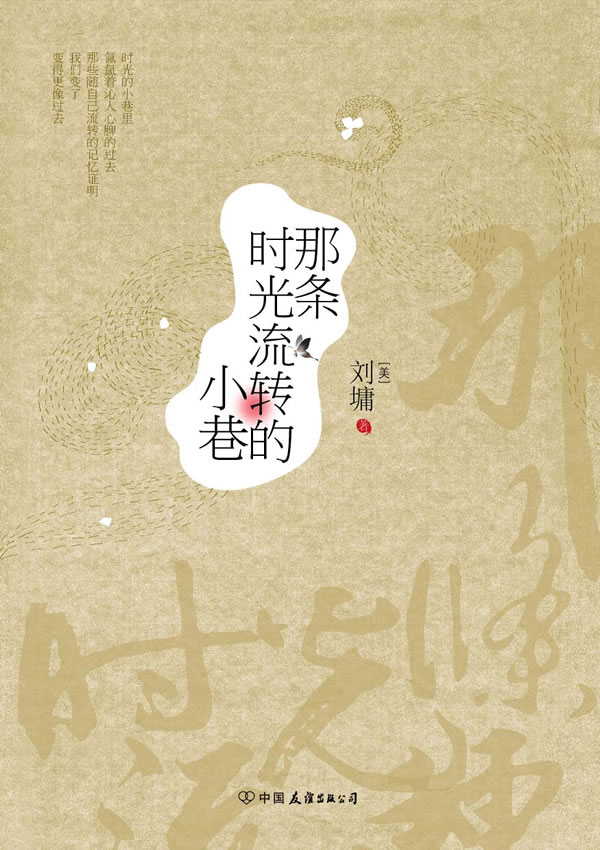
时光流转
刘墉
夜里飞临北京,由于机场在郊外,只能看见疏疏冷冷的灯火。
飞机落地了,周围的灯火变得稍微清晰,却又像萤火虫似的一明一灭。仔细看,原来那灯火是隔着树映出来的,民宅的灯光本就不亮,被树遮掩之后就更模糊了。树摇,灯火也摇,明明灭灭的,如一群群的星星。
突然有一些激动,不是激动于到了父母出生的地方,而是想起我的童年,童年的那条小巷!
那时的台湾,一条几十米的巷子,见不到几盏路灯。刷了柏油的黑木柱子,上面顶个圆盘似的灯罩,和小小的灯泡,灯泡还忽暗忽亮。
巷里的人家都种着树墙,那种用七里香围起来的“象征式”的墙。墙里有院,院中又有树,加上日式房子的窗棂小,屋里的灯火,隔着一重重,就更照不到巷子里了。
就是这似可见似不可见、迷离如梦的巷子,孕育了我的童年。
吃完晚饭,天将黑的时候,母亲常会让我出门,在她规定的范围内玩耍。
我活动的范围,是以电线杆为界的,向右不能过第三根,因为过去之后是温州街,车多。向左不能过第二根,因为过去有一家,出了两个太保。
小黑巷子里,是最适宜玩“官兵捉强盗”和“躲猫猫”的。尤其是各家的树墙、院子,任我们穿梭,更有着一种神不知鬼不觉的妙处。
当然,在这穿门越户的过程中,也便有些“向帘儿低下,听人笑话”的机会。
我家左邻,是位将军,那屋子里的排场,就又是一番了。我最怕听见他清喉咙的声音,有时玩“躲猫猫”,藏在他家树丛中,突然听见“哼”一声,接着窗子拉开,呸!一口浓痰飞出来。
至于对门,是位教授,教授的爸爸是知名的书法家。有一阵子,孩子们都不敢往他家院里躲,因为老爷爷死了,那教授总躲在房里哭,呜呜地喊:“阿爹啊!阿爹啊!”
也就有小孩绘声绘色地说,看见一个灰灰白白的影子飞进窗子。
黑黑的小巷里,除了飞蚊子、飞萤火虫,还会飞一群群的蝙蝠。才入夜,就见一团团黑影,在路灯下盘旋,有时候从头顶掠过,扑啦扑啦地,能吓人一跳。
孩子们常拿雨靴,往天上扔,因为不知听谁说,蝙蝠一看到靴子,就会钻进去。
没见过靴子抓到蝙蝠,但我打中过一只,见它斜斜歪歪地跌进河边草丛,小时候胆子大,钻进草丛,硬把蝙蝠摸到了。得意地拿回家,把蝙蝠塞进玻璃瓶里,紧紧拧上盖子。
第二天,蝙蝠不见了。
黑黑的小巷,也是耐人“寻芳”的。
黑暗中,什么都隐藏了。龙柏成了黑黑一团;槟榔成为瘦瘦一根;扶桑花白天开,夜里全睡了。倒是各种白花,变得特别清晰。
我家阶前,有棵单瓣的白茶花,冬天我最爱躲在树下,看上面洒下微微的灯光、月光,再嗅嗅那似有似无的幽香。
斜对门李家的院里种有茉莉。我至今喜欢一种粉红盒子的法国香水,觉得女人喷上这种味道,都美,大概就因为那香味让我想到童年的茉莉。
至于昙花,就更美了。
我家前院种了一大棵,每次夏夜盛开,父亲都会在院子里挂上灯,四处呼朋唤友,来赏吉兆“国泰民安”的昙花。
我爱那花,也爱那灯,觉得在一串灯中,人影晃来晃去,真美!那种影子忽大忽小,灯火忽明忽暗,人声忽来忽往,夹杂起来的感觉,好像梦境。后来读辛弃疾的词: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我心里映起的,就是这迷离的画面。
我常想,“时光流转”或许就是这样。在朗日晴空下,是见不到时光流转的。只有我童年黑黑的小巷,每一盏灯,都能映出一条条影子,忽长忽短、忽胖忽瘦。也只有在那小巷穿梭的记忆中,找到的哭声、笑声、倒水声、麻将声、吐痰声,和打小孩声,是那么幻中有真,真中似幻,值得我一生咀嚼、一生回味。
多美啊!迷离的灯火、往日的情怀。
多美啊!那条时光流转的小巷!










